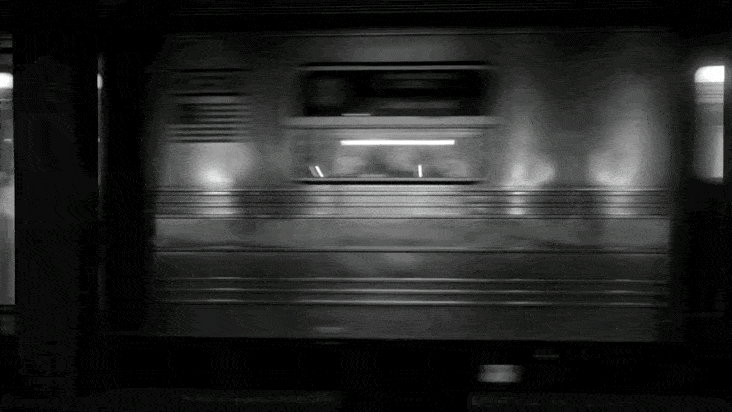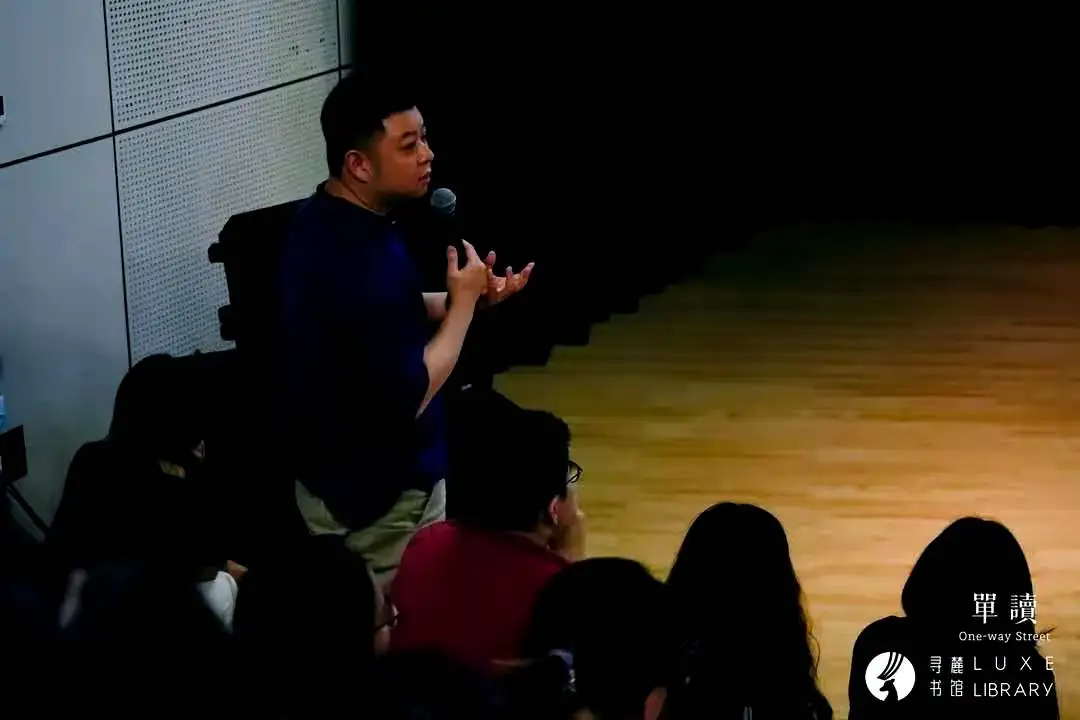在旅行的时候,我们的计划一再被打破,我们会一直忍耐,说服自己接受现状,继续前进。毕竟古语有云,“万事皆有因”。正是在这种妥协中,我们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惊喜,跳出旅行,获得新的灵感。
比如我们的《单读26个全球真实故事》。
《单读26全球真实故事集》可以说是从一次旅行中诞生的。随着这本新书的分享,《单身阅读》主编吴琦也从5月份开始推出了一系列旅行计划——旅行出发,旅行归来。
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单身阅读26个全球真实故事来到成都鲁迅图书馆和重庆经典书店。编辑吴琦邀请了自己的好朋友:翻译家陈颖、翻译家何、播客《早晚更新》主播任宁以及与“旅行”密切相关的四位创作者,来谈谈旅行与创作。
那么,是“边旅行边创作”还是“边旅行边创作”呢?让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旅行中创作的高清图片。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旅行中创作的高清图片。 #01
把“真实的东西”放在这里
它有自己的力量。
任宁:我想问问吴奇这本书的情况。如果把“全球真实故事集”这个标题拆开来看,全球化意味着某种多样性和联系。真理在我看来是一种力量;故事背后有一定的价值,一个能吸引人阅读的因素。你觉得哪个概念最让你感动,全球,真相还是故事?
吴奇:毫无疑问是真的。我觉得过去的“单读”很喜欢全世界。比如我之前在法国和英国访问一些文学机构和作者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抽象的“全球”概念吸引了我。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所谓的世界主义和全球化。当然,在这个阶段,在某种层面上,我们还保留着这个所谓的标签或者符号,但就我内心的秩序而言,它已经被排到了后面。因为似乎不再有一个抽象统一的地球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地球仪,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残酷得多,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寻找“地球仪”,但这暂时不是我们可以马上处理的问题。
故事是我最难驾驭的部分。我自己不写故事,在成为记者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太擅长用振振有词、引人入胜的方式讲故事,这可能是某种不足。以前喜欢写评论,后来喜欢描述,描写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可能没有剧情,但却是一个非常静态的画面。故事并不是我通常意义上最敏感最激烈的领域。之所以放在这里,可能只是因为它有一个替代“非虚构”或者“记者报道”的功能。
之前我们在思考题目的时候,总会想到真理这个词。当时想了很多“真实”、“真实”、“后真实”之类的词。虽然你可以无休止的处理这个概念,但是处理的时候会有一种怠慢,因为它不需要你过多的定义和限制。当你把“真实的东西”放在这里,它就有了自己的力量。虽然有时候“实物”并不是最好的形式。
比如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我提到了亨利·詹姆斯小说里的故事。他写了一对陷入贫困的贵族夫妇。因为没钱,他去一家插画工作室找了一份模特的工作。那时候插画师一般会画一些贵族家庭。夫妇俩觉得自己原本出身贵族家庭,衣着举止都是真正的贵族,认为画家会很欢迎他们。然而,画家在尝试后发现,他能更准确地捕捉到流浪汉、服务员或在餐馆洗碗的妓女身上的富豪风范,却无法在真正的贵族身上找到他想象中的贵族气质。所以,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讲,有很多角度和格局来讲道理。但是在实物面前,你无话可说
#02
红薯是你的马蹄铁。
吴奇:你在过去的旅行中是怎么玩的?你在找什么?有没有想过把旅行中的一些东西,或者你认识的人和事,变成某种创作素材?
任宁:感觉旅行中会进入某种“创作状态”。不谦虚的说,我喜欢的想法和作品,大部分都是在旅途中完成的。我觉得处在一个不寻常的环境中,那种状态给你的刺激能给你带来新的东西。但是去一个地方多了,兴奋感就降低了。
比如我去北京,可能这几年去北京太多了,到了北京没有异乡的感觉。飞机门一开,电梯门一开一关,我就去开会,去办事,完了就回去。上一次北京给我印象最深是去年年底,我去看吴奇。当时他们举办单行道书店文学奖,我却误把日期搞错了,提前一个月去了。到了那里,我跟他说:“为什么这个活动这么低调,没有宣传,连个易拉宝都没有?”他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北京。”他说:“嘿,现在不是11月吗?”
我来到这里,他来接我,喝了杯咖啡。那天我和他聊得很开心。会议结束后,我从一个月后将是会议地点的地方走回酒店(为了方便参加这个活动,我特意在旁边订了一个酒店)。在路上,我经过了北京的通惠河。这条河本身很普通,但是去年年初网上流传了一些照片,包括一个人躺在那个雪窝里很放松的照片。去的时候是冬天,没有下雪,但是想到了这一幕。
我在通惠桥桥头买了一个烤红薯,站在那里吃完了。吃完后,一块红薯肉从桥上掉到了河里。当时河水结冰了,所以摔在冰上。河水是蓝黑色的,烤红薯的肉是亮黄色的。我觉得这一刻的闲适有点像这烤红薯的肉,那么小,在整个暗黑色的背景上,像一颗火星,但它已经凝固在那里,有了自己的存在感,虽然对于这条河来说很小。我觉得旅行给我的感觉是,我还是我,我还是在用自己的状态和价值观去应对这个世界,无论我走到哪里。但这一次,这种新状态带来的位移和刺激,就像地瓜肉一样。虽然是异物,但是很奇妙,能给我带来不一样的东西。
何:我觉得你应该特别热衷于和吴琪聊天。直到最后,你走在河边,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时刻,在一个对你来说已经很陌生的地方。这突然让我想起李渔的一句诗——“归来不放烛红,待踏马蹄清月夜”。突然想到雪景是你的马蹄月夜,那红薯是你的马蹄月夜。
有时候我也是。我的马蹄月夜发生在大理的一个早晨。去年9月去了大理,在洱海旁边租了个便宜点的房子。当时我的翻译工作特别重,就想换个地方,待两个星期左右,写文章看海,赶紧把欠的债补上。走之前,我给一个比我小10岁的女孩讲了这个故事,她说,我能过来和你一起住吗?我说好的,过来。她非常活泼。她想去洱海周边转转,去大理周边玩玩,去探险。我想来这里,而这个女孩又那么活泼,我也是一个很活泼的人,所以我就去和她一起探索。结果我的债没有还清,所以最后几天,我每天早上四点就要起床,爬到租的房子的楼顶,抱着电脑,看着太阳一点一点的升起,开始赶稿子。
很多时候,当我赶着写稿子,看到太阳一点一点升起的时候,我会突然关闭翻译好的文档,新建一个空白色的文档,写下我此刻的想法。可能和太阳无关,所以把眼前的风景写下来,比如一只斑鸠飞过,写下来。这时候也会有马蹄清月夜的感觉——在非常忙碌的旅行行程中,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虽然早上那个时间起的比较早,比较困,但是很治愈,那个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03
我看到了这一幕。
我突然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
何:最近翻译了一本叫《川菜》的菜谱,很大很红。里面多次提到自贡。作为一个四川人,以前没去过自贡,所以去了。我们原本计划在自贡呆三天,但是第一天就去了自贡所有的景点,剩下的时间就开始在自贡的大街上走,去更小的地方参观。比如自贡有一道名菜——桥头三嫩,在很远的桥头镇。
傅夏(《川菜》作者)在大桥桥边写了三个嫩菜,写得特别生动:一口大锅,有很多油烟,厨师把菜做好以后,倒下去用大油炸,就像爆炸一样。所有东西都炸了15秒,然后起锅。当时我站在一个小门前,看着厨师炒菜。他的行为和文中写的一模一样。我通常会把作家的话重新写在纸上,但现在我看到眼前的这一幕,立刻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
#04
北京是一个中心感很强的城市。
吴琦:北京是一个中心感很强的城市。也许上海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在一个中心感很强的城市,很容易不自觉地产生一种焦虑感。即使现在我也有点怀疑。网上流传的“内卷”、“平躺”等词,主要是指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的人的状态。所以这些词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概括力。
我最近很努力的创造了很多出差的机会,包括去福州,苏州,杭州,广州。每次旅行都让我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放松和鼓舞。解脱就是松开螺丝,把自己从需要坐在一起上课、开会、同时做很多项目的状态中拉出来。另外,每次旅行,我也有思考和观察问题的角度的提示。似乎我过去把北京对世界的看法等同于我自己的看法。这种视野可能很大很广阔,但也遮蔽了很多东西,很深刻很享受,只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隐藏了。
创作旅行
#01
旅行和创作可以互相奖励吗?
吴琦:陈老师能不能谈谈他的一些旅行习惯,在旅行中做一些有创意的工作?你是怎么把旅行和创作结合起来的?
陈颖:我最喜欢的旅行是在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体验当地人的状态,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
比如我最喜欢的城市是巴罗莫,那是西西里一个特别阳光的地方。每次去那里,我都假装是意大利人。去酒吧喝咖啡,也点一杯咖啡,站在那里默默喝完,体会意大利人的感觉。这是我喜欢玩的游戏。当我去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假装是当地人。
所以如果真的去揣摩对方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在东欧的时候,也给了东欧这个名字。有了名字就可以直接隔离出新的人格。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我不会在那里扮演我自己。我想演别人,演一个东欧姑娘。这是一种玩游戏的方式。
吴琪:太可爱了!
陈颖:虽然这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种进入当地文化的感觉和当游客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自暴自弃的过程。有些人只是执着于自己的现实生活,但如果你稍微放弃自己,去看看别人,你会和别人形成一种交流,你会有新的收获。旅行也是一个开放自己的过程。一开始你有一个东欧名字,但这个新身份会逐渐给你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吴琦:那么在翻译和创作的过程中,这种去当地,实际生活在那里,被肉眼感知的体验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呢?
陈颖:旅行和创作的关系太密切了。先说创作。现在我正在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上为杂志写关于中国主要城市的文章。我感觉如果只是去过这个城市,根本写不出来他们。但是如果我活的时间比较长,至少三到五个月,我还是能写出比较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和我的写作是直接挂钩的。我觉得临场感很重要,包括我们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和网上的交流,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可能带来的感受的强度也是不一样的。
吴琦:我对陈老师刚才的分享深有体会。几年前我去巴黎编辑《单身阅读23:破屋》,我也在做《下一次会火》的翻译。我偶然在当时的《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记者重走鲍德温从法国到瑞士的路线,特别聚焦他在巴黎的流浪,而巴黎恰好是我生活的地区。
所以我试着根据地图去找。比如他会去花神咖啡馆,一路跑到麻黑区找夜生活,住在公园旁边的小旅馆。我其实是漫无目的的闲逛。不知道要找什么,也没有具体的任务。我不用为了解决一个难题或者找一个词而工作,但是我发现这会和工作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互补和碰撞的过程。
我想这就是刚才陈先生说的。旅行和创作有时会相互奖励。并不是说你有意识,你不用去任何地方完成你的写作。而是当你自己的人生展开的时候,那些偶然的发现会连成一幅有趣的地图,最后拼凑成一个意想不到的样子。
#02
在干燥状态下吸一口气。
吴琦:刚才我们谈到了旅行和创作。我觉得在中国旅行会帮助我们打开很多思路,帮助我们克服在大城市生活的“干燥”状态。这种干燥不一定是气候意义上的干燥,而是我们生活状态中的一种干燥,比如每天被无穷无尽的事物、项目、死亡驱逐的状态。不像在成都和重庆,在北京生活有很多水汽,很多空,有很多可以不断咀嚼回味的空余时间。这些是帮助我们像鱼一样从水中呼吸的即时营养物质。
陈颖:我觉得每个人和城市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反思我们与城市的关系,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来理解我们周围的生活。当然,读书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比如北京,我觉得北京是一个需要全力以赴的城市。你要么全力以赴,百分百对待,要么就离开,所以我选择了毕业后离开。不过重庆对居民的要求没那么高。如果你住在这里,即使和它若即若离,也是可以的。
这让我想起了卡尔维诺,他在巴黎生活了很久,但他的状态与巴黎非常隔绝。他住在乡下的小别墅里,在那里工作,偶尔去镇上买份报纸。有时候我会在巴黎呆一段时间。第一次去巴黎,那是一种真正的初恋的感觉。我满怀激情地看着城市里的一切,看着雨果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看着波德莱尔吵架的地方。当时的经历很多。
但是如果你以后去了,你会觉得你在那里工作,所以仅仅是在公园里转一转,跑一跑,并不会建立起和一个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感觉。为什么我最后不能和巴黎建立深厚的感情,主要是因为我法语不好,这也是一个很深刻的原因。我的法语仅限于很浅的聊天,但我无法和当地人继续聊下去。所以真正的旅行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不仅是语言方面,心态方面也是。你需要强大的力量来面对这种无力感。
#03
在别人的世界里游荡太久,
将在某人的脑海中
吴琦:陈老师翻译过很多作家的作品,每个作家的语言和文笔都完全不一样。比如我翻译鲍德温的时候,经常觉得这句话好像是我能说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太熟悉或者太认同作者的语言,以至于有时候会突然和作者融为一体。
陈颖:当然有这个经历。每个人和现实的关系不同,导致对文字的感受也不同,包括他想表达的,不是我想表达的,所以要把译者和作者分开。
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作者-译者,你必须完全放开自己。你要把自己关在一个小盒子里,进入他的世界。这是一个很累的过程。同时,你完成工作之后,也要有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因为你好像有点失落,在别人的世界里徘徊太久,就会情绪化。这种经历还真不少。有时候,我上午下班后,会情绪激动一下午。然后你需要找到自己的情绪,找到真实的自己,然后去面对原本的生活,但这也是一种比较私人的体验。
-关于单身阅读周末-
2021年上半年,单读书几乎马不停蹄地奔向各种新鲜事物。
如果还有什么想尝试的,那就是去各个城市,和当地读者面对面交流。
“单读周末”开始了。
利用周末,入侵你的城市。